在上篇回泰瑞的 comments 中,我提到四部本一家。為什麼會這樣說?好比說,四庫全書不就是經史子集四部嗎?怎麼會混為一談呢?這或許應該從四部的淵源說起。
中國學術,雖分四部,然經學最早。在經學以前,其實只有詩、書。書只是一些政治文件,然而詩三百則流傳至今。易經雖自古相傳,但是古時只是卜筮的書籍。換句話說,在上古時期,學術是不流通的,只由政府最高層主掌。所以孔子當年才會說,「春秋,天子之事也」。
開啟學術流通風氣之先的,正是有教無類的孔子,開啟了私人講學風氣之先。到漢武帝時,以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春秋為五經,設立五經博士。從此以後,各代經學,只有傳述,沒有增添創作。經學所講,也不出周公、孔子的理想與實踐。那麼經學在漢朝,豈不正是史學?春秋為五經之一,但是春秋也是第一部私人撰寫的史書。因此,我們也可以說從漢朝開始,經學即是史學。
回到子學。先秦諸子當中,孔子開私人講學風氣之先,遂儒家先起。然而在學術思想大鳴大放的戰國時代,最先有經的是墨家。論語編篡,則在孟子之後。其他各家,更在儒墨之後成書。但是即便是為儒家開山的孔子,也常稱道周公文王。後代儒家則更上推到堯舜禹三代。墨家則說,「非大禹之道,不足以為墨。」道家在之後而起,但是更上推到黃帝。至於陰陽家、農家,無不取法中國上股相傳的帝王。等到秦朝統一天下,贏政自稱「始皇帝」,也是從春秋十二紀來的。如此說來,先秦諸子的淵源,全都是由史學而來。
到漢代太史公著史記,也自己說「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。」正表示太史公寫史記下來,原意也是為了跟先秦諸子一般,自成一家言。從太史公以降,後世二十五史,也無不成自家言。子學史學,實在沒有多少分別。
再論集部。像先秦諫逐客書、漢代的治安策,豈不是當時著名的奏議文?不也可以納入集部?三國時代的建安文學,如曹操的奏議詔令,或者是諸葛亮的出師表,不也適合收在集部?但是其一人的作品,正是他自己一家之言,也是一人之史。那麼這些作品,不也屬於子學、史學範疇嗎?就算退一部說,經書的詩三百,在古時候不也正是集部?論語雖是子部,但也屬於集部。如此說來,集部只是較為單純的子部而已。
總體來說,中國學術雖分四部,但大體不分子、史兩途。然而子部又由史學衍生而來。子學教你做人的道理,史學教你做事的道理。一內一外,相輔相成,渾融一體。這也是為什麼孔子會說,「吾道一以貫之!」因為確實就是「一」啊。
參考: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、《中國史學發微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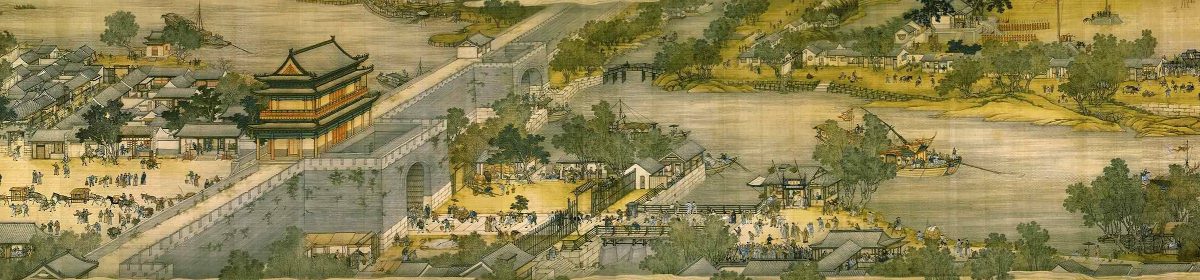
 剛剛在
剛剛在